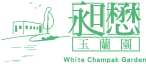從宜蘭看天下

【自由的疼痛:從瑪麗亞.科里納.馬查多看台灣的民主遲鈍】
◎文/劉哲廷
二〇二五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五十八歲的委內瑞拉政治家與人權運動家 — 瑪麗亞.科里納.馬查多(María Corina Machado)。理由是她「為委內瑞拉人民不懈推動民主權利,並為實現從獨裁到民主的公正與和平轉型所做出的努力」。這是極少數屬於「未竟之事」的獎項。得獎者尚未迎來勝利,國家仍陷於黑暗,而她代表的,是一種尚未完成的希望。
她走過被驅離國會的午後,被禁止參選的宣判,被國家機器追捕、抹黑、封鎖。她沒有退讓。她的身體是拉丁美洲最赤裸的民主記憶,一個人的意志在整個體制的陰影中,仍以呼吸的節奏維持微弱卻持續的對抗。這場對抗不是劇烈的反叛,而是無數日常的延續:開會、演講、被取消、再回來。她的勝利不是奪回權力,而是拒絕絕望。
諾貝爾委員會說她「為實現從獨裁到民主的和平轉型努力不懈」。這句話聽起來像例行公事,但它指涉的是人類最難的事:在失敗裡繼續相信政治。委內瑞拉的民眾在長期貧困與壓制之下,對制度已不再懷抱期待,民主成了一個遙遠的語言,而她仍選擇留在那個語言裡。她沒有被擊敗,只是被延遲。
台灣的民主正好相反。我們的自由太早成功,以至於我們不再相信它需要被維持。我們的公民社會被選舉節奏磨損,投票變成慣性,表態變成反射。人們熟練地切換立場,用網路表情取代思考,用諷刺掩飾恐懼。在網路暴民的匿名喧嘩裡,我們是否默默接受了「多數即真理」的暴力?這不是獨裁,是過剩的自由導致的遲鈍。
馬查多的勇氣來自一個失敗國家的廢墟;我們的倦怠卻長在穩定繁榮的溫室。她必須抵抗政府的暴力,我們只須克服自己的冷漠。這種對比讓人尷尬:台灣人經常自稱「亞洲民主典範」,但在民主運動減少後,我們的熱情也迅速冷卻。民主對我們來說,不再是動詞,而是完成式的句子:我們「已經」自由。
然而,真正的民主從來不會完成。它需要不安,一種願意懷疑權力、質疑同溫的能量。當公民不容再被冒犯,民主的語言就開始衰退。台灣的政治語彙正逐漸被情緒化、娛樂化的語法取代。討論變成表演,憤怒變成姿態。我們在言語上激烈,精神上卻極度順從。這種「假參與」的文化,是民主最危險的幻覺。
馬查多的意義,在於她讓我們重新理解「公民」這個詞的痛感。公民不是群眾,也不是粉絲。公民是能在情緒中維持清醒的人。她所面對的獨裁不是偶發,而是一種體制性地毀壞真相的日常,而她的抵抗正是恢復現實的一種努力 — 提醒人們還有另一種時間、另一種說話的可能。
台灣在表象上擁有一切:新聞自由、公開選舉、政黨輪替、網路言論。然而我們的問題在於這些自由的形式已被空洞化。媒體在利益下失去立場,政治人物操作情緒取代政策辯論,民眾對公共議題的關注被轉移到短視頻與輿論戰的即時快感。這種民主的空殼,讓我們看似自由,實則遺忘了自由的疼痛。
自由本該讓人痛。痛在它要求我們持續參與、持續懷疑、持續檢驗那些以「多數」之名說出的暴力。痛在它要我們為不方便的真相辯護,即使那真相會讓朋友離席、讓陣營分裂。痛在它提醒我們,政治從不是舒適的事,而是對現實的不斷打磨。
馬查多沒有讓委內瑞拉立即變得自由,她只是讓人記得自由尚未死。這樣的記憶,比勝利更重要。台灣也需要這樣的記憶,以防我們厭倦了政治、討厭投票、對公共事務冷笑,而那正是民主開始衰退的徵兆。
(作者是詩人,自由工作者,摘自2025/10/11自由廣場-社論)
(攝影/Nobody 看見宜蘭)